2003年至今,刘擎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是每年都会写一份“西方年度思想述评”。参加综艺节目,让他获得了学术圈之外更多人的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对这项工作懈怠。
作为公共人物的刘擎,希望能够与年轻人建立沟通,想要与他们有更多的交流,想要在匮乏的时代里找到一些意义。作为学者刘擎,想要把自己的研究完善,想要写出更好的思想述评——更多的关注给了他更大的动力。
翻看他十八年来的思想述评,我们会看到那些在新闻里出现过无数次的瞬间,这些瞬间一点一点地塑造了裂变的当下。

我们和他聊了聊略显悲观的西方思想界,以及年轻人眼中的未来。
采访 | 程迟、重木
编辑 | 郝汉
我们终于在落雨的杭州见到了拖着小行李箱的刘擎老师,接受完我们的采访之后,他还需要赶往另一场活动——这已经是他生活的常态了。
刘擎老师通过《奇葩说》从学术圈“出圈”之前,他每年的“西方思想年度述评”是他在学界的一张“名片”。他坚持写“年度述评”的十八年,也是世界产生巨变的十八年,我们会看到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欧盟危机、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上台等路标式事件给西方思想界带来的震动与改变。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在刘擎这些年来的述评里,我们看到了世界缓慢的“裂变”。从2003年开始书写的时候,全球化一路高歌,到近两年似乎有所退潮,在北美和欧洲都遇到了挑战。
当2003年到2019年的思想述评都呈现在一本《2000年以来的西方》里时,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冲击。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那些遥远的事情?西方思想界的变化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掌握了力量的知识分子,又怎样改变了当代生活?我们有太多问题想问刘擎,但是隐隐地担心他紧张的行程以及过多的媒体采访已经磨损了他的表达欲。
但是,从他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开始,我们就知道,他还是那个时常站在讲台上,耐心听完问题后,真诚地与学生交流的老师。他不是在回答,而是在交流。
西方思想界比以往更悲观
硬核读书会:您坚持写“年度西方思想述评”已经18年了,从2003年到现在一直记录和观察中国与西方。我看到您的思想述评中,2018年开篇的第一章叫《动荡世界的迷宫》,2019年是叫《近身的世界》, 2020年的序言叫《漫长的告别》。
最近这三年的西方思想述评,让人感觉有一种悲观的情绪,其中的一些表述会给人一种无奈感,您会同意我这样去理解吗?
刘擎:很准确。因为这是关于西方思想界的述评,其实这不是我个人的悲观,是要传达西方思想界的整个气氛。这个气氛可以叫做后冷战模式的破产或者崩溃之后,带来的动荡不安和不确定。
所谓后冷战模式,就是冷战之后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竞争已经基本上game over了,就是“历史的终结”。大概从90年代年苏联解体之后,一直到2001年的911事件,西方世界都在遭到冲击,但是它马上就恢复。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非常漫长,那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质疑、批评、怀疑的声音。
2014年开始出现脱欧的现象,在欧洲有像德国“另类选择党”这种右翼的民粹主义兴起,再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冷战之后西方对自由主义必胜的确定性的信心在摇摆。经过911的打击,2007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到最近几年西方直接出现政治上的动荡,这样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变化,它传达到思想界,西方思想界的基调比以往悲观。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刘擎 著
一頁丨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4
硬核读书会:您的西方思想述评写了18年了,您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段?西方世界发生的哪些变化对全球影响最深?
刘擎:西方世界的变化,我觉得和国际自由秩序曾经的过度扩张,以及它现在的收缩有关。
剑桥大学政治学家润斯曼( David Runciman) 提出过“民主信心的陷阱”的说法:民主的问题是,民主很容易让人自满,然后一旦发生危机,它又让人觉得民主马上就要崩溃了。
民主政治在历史上不止一次有这种摇摆,好的时候过度自信,这种过度自信,就倒向了失败,结果,成功就变成失败之母,然后相信民主崩溃的声音就强劲了。现在美国就进入这样一个周期。你看它三十年前“历史终结论”时的信心满满,到现在整个对民主的态度特别消极。所以那位学者认为如果从长程历史来看,人们对民主的看法总是在“必胜”和“必败”之间有一个左右摇摆。
它给我们的教训或者说启示是说,民主,或者说任何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转,都不是现成的。民主是一个实践展开的过程,就像每个人的生命一样,是一个要不断making和remaking的过程,所以要把它看作是类似于生命的过程,而不是一台机器。
生命会受伤,会有疾病,可能会感染病毒,因为环境在变,它自己可能做了冒险的事情,导致了失误,不够审慎……等等。而且,民主政治的成败涉及人的意愿和特定的政策选择,这都是认为的因素,没有什么能确保它是必胜的,也并不是必然崩溃。
硬核读书会:在您写的书评里面,美国占着一个非常大的比重和位置。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诱惑》最后一章写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论”,他说其实这些知识分子对美国想象很偏颇,反映的可能并不是美国的实际情况,可能只是他们自身的焦虑。
《非理性的诱惑》
[美] 理查德·沃林 著,阎纪宇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7
刘擎:客观上,美国在全球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它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技术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现在仍然有一个美国霸权在那里。无论你是喜欢美国、反对美国、怀疑美国,你都无法无视它,美国仍然在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界定着世界秩序。只要美国这种影响力客观存在,它就会成为一个瞩目的对象。当然,欧洲也是这样。
但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关注与对它的客观认知不一定成正比。比如,有人对美国会盲目崇拜,有人相反则完全愤恨,这里或多或少是自身焦虑的折射或投影,不只现在如此,在整个近代历史上都是这样。
对“知识偶像”这个词,我是排斥的
硬核读书会:您聊到过国外的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这种文化和中国其实也存在,比如在明星粉丝圈和互联网上。您觉得这是Cancel Culture影响到我们,还是说这是一个新生代的自身的力量?
刘擎:这是全球性的,是因为有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新形态造成的,以及,这一代年轻人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
以前有一个精英主义的文化生产,它是有门槛的,比如纸媒等各种主流媒体,它有专业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定位、自我确证的这样一个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边缘的人只能自己在私下议论,没有多少公共影响力。
但是,自媒体出现以后,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权重一直在下降,无门槛的各种各样的意见表达得越来越强劲,这就打破了以往精英主义对公共话语的垄断。因此在公共领域,众声喧哗,变得更无序了,也可以说变得更多样化了。
其实这种Cancel Culture是一种“取消”或“封杀”的力量,虽然它并不是通过公权力让你噤声。整个互联网空间,它是另外一个社会空间,这是对人的观念、想法、情感和认知影响很大的社会空间。
在其中很多人能够迅速集结起来,形成一种力量,能够起到“取消”的力量,这是一种由新技术带来的全球性现象,也会受到这种技术条件的制约。
美国近年来出现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有色族裔抗议美国社会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硬核读书会:传统知识分子以前是通过纸媒等媒体输出观点来影响大众。现在像您这样在高校的教师,面对新型的、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交时代,您是否觉得冲突或者矛盾?
刘擎:主流媒体哪怕在网络上也会受到一种专业主义的传统传媒标准的检测,而社交媒体几乎不用,所以你会听到以前听不到的那种反馈,无论是正向的还是批评性的,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对知识分子作者的一个压力。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现在这种大众传播的新的方式,来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硬核读书会:在《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里有一个部分写到区分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您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更接近哪种角色?你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意见的给予者吗?还是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
刘擎:这是年代述评中讲“思想工业”的那篇文章提到的,其实也是综述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它跟当下的状况有相关性,就把这一节摘出来收入了这本文集。
现在出现了“思想工业”的这种市场,为那些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愿意发表自己对社会和公共话题见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机遇,这扩大了他们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同时也受到市场逻辑的制约,其中的关系特别复杂。比如,学者“出圈”是一种新近的现象,我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认知。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是,市场力量是否对学术自主性造成影响。
我并不特别关心自己的形象,但对“知识偶像”这个标签我自己是排斥的。我只是希望自己能保持警觉,警觉知识和思想在通俗化的过程中可能变得碎片化和平庸化。所以,我反复强调过,不要盲目信奉某个名人的见解和看法,而是要对开启的问题展开自己的深入阅读和思考。
比如,我写的讲义类的书籍主要是起一个“导引”作用,初衷是希望将读者引向更深刻和更系统的学说和著作。我其实并没有把握自己对年轻人的导引是否有效。人们能得到启发和线索,然后自己去阅读和思考,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当然,有些读者可能就是把这类导引书籍当作消费品,消费一下就结束了,并不在乎背后来龙去脉、背后更系统性的知识和思想以及更深厚的资源。他们可能只是觉得某句话,某个段落引起了共鸣,或者获得了抚慰,或者激发了兴趣,或者提示了新的角度……
这样一种消费方式好不好呢?我觉得这不够好,应该鼓励他们更进一步走向深入。但同时,我也不认为特别有必要去鄙视或指责这种“浅尝辄止”的消费态度,因为对于知识学术性的产品,“浅尝辄止”比“置之不理”或许还是好些吧。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刘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4
硬核读书会: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像严复和杜威这样的学者,他们做的事情和您有点相似,就是把国外的东西翻译到中国,让一些思想在大众中传播——虽然大众可能也算是一个比较精英的大众。从小众的关注,到现在大众的关注,您觉得书里面写的内容对大众的意义是什么?
刘擎:我完全无法和严复或杜威这样人物相提并论,即便有些工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本来我的“年度述评”系列的目标读者只是学术圈内不同专业的同行,因为其中讨论的关于当今世界的问题涉及的学科是各种各样的,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文化理论等等都可能涉及,主要就是给宽泛意义上的学者同行提供一个便利。
也就是说我自己去汇集资料,然后做加工处理,最近几年也更多地加入了自己的观察和评论,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相对来说个人化的和短小的类似年鉴的作品。
现在这个年度述评的汇编有了更多的读者,超出了学术界。我想,这是因为西方的思想状况的动态影响了西方社会,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一些动向,而这些动向又会影响到中国——不只是知识精英,也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比如说手机制造业的工厂,无论是工人是还是工程师,他们工作前景会与中美关系发生关联,与技术进口的限制有关。
所以,我在2020年的述评中写到了“生活本地性的瓦解”的问题,就是没有任何地方的生活是单纯“地方性的”,这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所冲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受到很多变量——特别是遥远的、我们不太熟悉的、很难理解的一些变量——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世界。这是一个复杂的局面,那么,对于那些想要理解和澄清自身处境的人,可能会通过阅读我的文章发现一些线索,去思考相关的问题。
比如许多家长准备送孩子去国外留学,我在述评文章中有一节介绍了美国亚裔组织起诉美国著名大学在招生中涉嫌歧视亚裔申请者的问题,那篇文章受到很多学界之外的读者关注。所以,这本书可能比我以前设想的读者群更大。
现在的人有一种匮乏感
硬核读书会:您和罗翔老师、许知远老师都是通过参加一些比较大众的娱乐媒体的节目,然后开始出圈。所以有好多人在讨论,传统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大众娱乐,他们和大众娱乐的结合,到底是好是坏。所以在您观察看来,现在传统知识分子进入大众传媒的时候,能体会到年轻人又焦虑又渴望的感觉吗?年轻人给您的回馈,您觉得大概是什么样子?
刘擎:这些学者、教师和作家,以前也并不是完全躲在象牙塔里面其他什么都不理会,我们也会参加公共活动,比如说读书讨论会,各种论坛和讲座等等。不过这些方式吸引的受众仍然是宽泛意义上的“知识公众”,大概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
但是现在因为参加了综艺节目,就“出圈”了,而产生的影响完全超过我自己预期,我也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为什么会如此。对于其效果,我认为利弊都有,这个问题我在很多访谈中已经谈过了。对自己而言,就是要保持谨慎判断。
刘擎在《奇葩说》。
对于现在年轻人的焦虑,我没有深入的研究,根据一些交流获得感受,我推测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过去的模式对年轻人不太有说服力,甚至根本不被信任。这个模式就是父母和老师相信的和倡导的,“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的那个模式。
现在的年轻人感到,他们和前辈——出生在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人不一样了,现在90、95后和00后的年轻人感到自己可能没有前辈曾经拥有的那种成功的机会,他们感到自己能够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努力奋斗的成本和时间越来越长。这可能是引起焦虑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竞争游戏当中,无论是成功的人还是不太成功的人、受挫的人,相当多的人有一种意义的匮乏感。就是想要问: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问题。
我们似乎没有一套让人信服的意义论述或叙事——关于生活的意义,无论是在学习和工作中,还是友谊和亲密关系当中的意义,于是,生活的意义好像枯竭了。
我们当然有一些从小就有的价值教育、道德教育,应该说许多老师为这些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从作为“接收方”的年轻人的感受来说,好像还没有找到特别有效的方式,这种教育还没有深入人心。
当然,我也并没能力给出一个确定的方法或答案,我只是认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值得思考和探索,然后我希望能对这种探索提供一些线索和资源。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努力获得现在年轻人的注意。
硬核读书会:您在去年的《十三邀》微信特辑里面讲到过话语的“童稚化”。我们也有很强烈的感觉,因为会看到大量的评论是同一种声音,是没有经过更多思考的声音。您在师范大学教书,就你的观察,在你的学生里面,这几年,比如说从2010年或者是从2000年初到现在,他们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刘擎:我觉得是慌张和焦虑感的蔓延,年轻人阅读耐心的下降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中国人口基数那么大,热爱阅读的年轻人哪怕比例再小,也还是有的。特别是像华东师大这样的985、双一流大学,总还是找得出来的。
我自己每年都会接触到很多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生一般还不错,大概有1/3到1/4的同学相当不错。在本科生中间,每年我都会发现四、五个优秀的“读书种子”,他们绝大部分后来都会继续深造,读研究生。但是整体而言,比如说,现在就会有学生在课堂上看手机,虽然在我的课极少出现。
曾有段时间我担任系主任,经常要去听别的老师讲课,有一次课发现许多学生在看手机。其实在我看来那位老师讲得非常好,主题经典文本的分析,那种“文本细读”的指导非常见功力,也有少部分同学对老师的评价很高。但许多同学觉得老师讲得“太枯燥了”。
我感到,学生们现在对老师讲课的“生动效果”要求非常高,因为他们对“枯燥”的耐受力特别低。老师要表达得生动,要有娱乐性的“段子”,或者有强烈的感染力,这才能吸引同学,然后你再讲的深入才会抓住他们的注意力。你看,现在老师好像必须成为一个艺术家、段子手,不然有的学生好像就受不了,就会转向自己的手机信息,有相当一批同学是如此。
刘擎在《十三邀》中谈“童稚化”。
人们对文字阅读的抗拒,基本是没办法改变的
硬核读书会:当年桑德尔的《正义课》是很受欢迎的,国内高校为什么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级的课程?现在罗翔老师在B站走红,他也讲得很生动,网上诞生了很多段子。为什么在哈佛正义课之后,就没有出现第二门引起全球阅读潮的严肃学术公开课?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这样的大学课程?
刘擎:蛮困难的。因为就像尼尔·波兹曼认为的,影像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文字不是人自然演化的结果,是文化演化的结果。人类在几万年以来,甚至再远一点,几十万年的进化当中,我们看的不是文字,是图像,听的是声音。我们是用非象征符号的方式直接感受世界,所以我们很适应,对这个东西很敏感很灵敏。
人类发明文字也就是几千年,更广泛阅读的状况则需要到教育普及以后。我们的现代文明建立在印刷术诞生、大众的识字率提高以后。这是很短的现象,两三百年。
所以,人被培训着去阅读、深入地学习,这是反天性的。这类事情需要训练,你需要有很高的回报,才会愿意去做,因为人在自发的意义上不会偏爱阅读。阅读要能够带给你很高的回报,是需要你达到比较高的、深入的境界,你才会喜欢它,获得那种满足。
这种情况基本是没办法改变的,我觉得。
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截图。
硬核读书会:您在这本书里写到了好多知识分子,比如说像萨义德、阿伦特、托尼·朱特等。因为最近的巴以冲突,大家又想起了萨义德。
其实您写那篇纪念萨义德的时候,最后也写道:在他去世之后,我们这个世界是靠我们自己去探索。您最近受到大家那么多关注和那么强的投射,会有这种感觉吗?其实我们是需要一个人的,需要有一个在那个位置上做这种事的人。
“启蒙知识分子”虽然是有点矫情的说法,或者大家不再那么看重,但您觉得在这种漂浮不定的现代性生活中,我们还需要这种人吗?
刘擎:当我们对现状不够满意的时候,可能特别需要一种启发性的知识人。他们不仅说另外一种生活是可能的,而且告诉你为什么是可以想象的。启蒙意味着一个alternative,或者一个出口。
像福柯那样,他在康德关于启蒙的论述中,不是找到了一个论点,而是发现一“出口”,一种作为精神气质的“出口”。这种精神气质就是,不需要也不注定在现在的轨道上一直走下去。你总是可以有一个出口,福柯让你看到这个出口,出口永远是存在的。
那么其实是需要一批知识人,在这样一个时代变化比较迅疾的时候,在各种各样特别复杂的因素造成不确定性混乱焦虑的时候,让我们静下来,让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另外的可能性。
《觉醒时代》剧照。
中国的读书人多多少少总有心怀家国的公共情怀
硬核读书会:像刘擎老师这一辈人,如布尔迪厄说的,你们有文化资本,就应该去做你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说矫情一点,应该是启蒙,就应该做萨义德、托尼·朱特、桑塔格这些人应该做的事。
刘擎:现在有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困境,因为知识分子自己也未必有启蒙的信心,自己也并没有确切的把握,断定哪一种生活是更好的,哪怕对自己是好的,更不要说对年轻人是不是好。而且时代变化太快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现在可能已经不适用了,就像我们上一代人,告诉我们的经验很多已经不适用了一样。
所以我自己的定位是,愿意跟年轻人一起来探讨。我说过,关于人生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导师,我可能像一个学长一样,我们是在过去一个时代上学,你们在新的时代上学,我们彼此可能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探讨、来对话。
如果你觉得我们缺乏像萨义德和朱特这样的人,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点是我们可能没有他们那样的信心。
硬核读书会:但是,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不谈,才导致没有萨义德和朱特吗?并不是公共领域先存在,我们再进去。
刘擎:对,你说的对,公共领域是需要争取、需要建设的,但建设依赖很多条件。有的人问我为什么要上《奇葩说》,我就说,这是我现在能看到可能的、可以做的东西,因为《奇葩说》与知识、思辨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公共领域,上一代学人跟年轻人应该有更好的对话和讨论。
我们的困境在于,第一,现在公共领域它不容易靠自己就建立起来,我们对自己的经验、知识和智慧也都没有足够的自信,而且在网络环境中讨论,会遇到情绪化的批评和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学者本来就有一个令自己舒适的、吸引人的“故乡”——躲进书本,这多有美好啊:读一本书就有一份心得,哪怕没有写出论文来,干嘛要去参与那么麻烦的事情?
但另一面,中国的读书人多多少少总有那种心怀家国天下的公共情怀,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人的纠结。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上一篇: 在万亿级别的癌症早筛市场,做一名科技创新的开拓者
- 下一篇: 这个神秘热搜背后,藏着流行歌难听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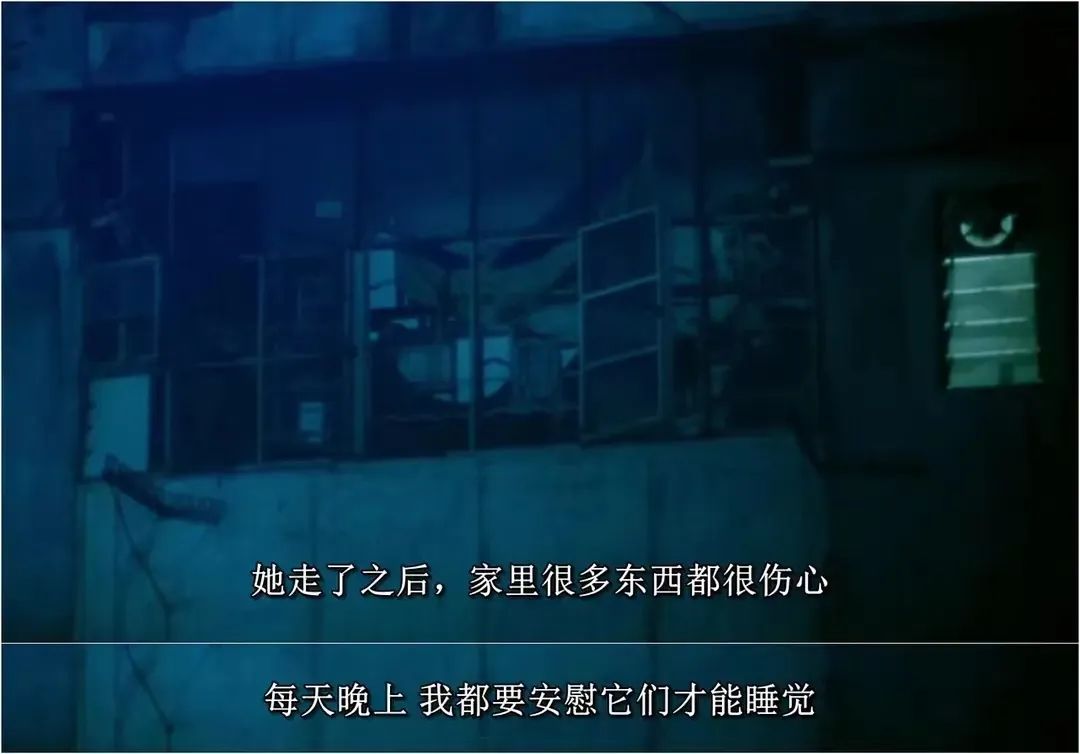







最新留言
说:写得非常好!
2020-10-28 11: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