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东然)

( 电影《雨果》剧照 )
故事大王的3D电影
《雨果》改编自布莱恩·赛兹尼克的《造梦的雨果》。这本书于2007年出版,2008年荣获美国凯迪克奖(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学会颁发给“最杰出美国儿童绘本”的艺术家)及《纽约时报》2007年最佳绘本奖,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一名,还入围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
马丁·斯科塞斯回忆,4年前是坐下来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的。“但我原本没联想到玩具店的主人结果会是乔治·梅里叶,这个结局对我而言何其精彩!我爱梅里叶,也略知他确实衰微和挫败了,最后在蒙巴纳斯火车站开玩具店16年,而这一切连起来便不仅是趣味,它关于电影的开始,关于一个小男孩对于机械的迷恋,当然以及我在十几岁的时候热心崇拜着的魔法,于我这是难以割舍的工程。”
事实上,1902年乔治·梅里叶执导的电影《月球之旅》也是作家布莱恩·赛兹尼克写出这个故事的起点,他对乔治·梅里叶的缅怀,则是作为一名绘本作家对令人血脉贲张的想象力的崇拜——一支火箭飞进月球(人)的眼睛,他(月亮)又痛又无辜地吐了吐舌头。
作者布莱恩·赛兹尼克如是回忆撰写这本书的开始。“这画面太迷人了,我便想要写一个故事来描述一个孩子遇见梅里叶的故事,但没想清楚情节的前因后果,直到2003年,无意中我读了盖比·伍德的《艾迪生的夏娃》,那是本机器人历史,令我惊讶的是,作者整整用了其中一章来梳理梅里叶的机器人发明。书里说梅里叶制作过的几个机器人(或者说是人形机械,由内部发条装置提供动力,能自行表演诸如绘画的一些功能)曾经捐给一家博物馆,后来遭遗忘,雨水侵蚀而终被丢弃。”

( 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电影《雨果》拍摄现场 )
于是布莱恩·赛兹尼克想到了一个男孩与损坏的机器人的故事,而乔治·梅里叶的人生故事则作为穿插,是故事内部最重要也最深情的悬念。这本书图文并茂,不完全是漫画书,也不只是绘本小说、翻书动画,更似所有这一切形式的结合。《造梦的雨果》一炮而红,毋庸置疑,素来对“家庭电影”青睐有加的好莱坞,这是不可多得的好题材。
出于对原著的喜爱,斯科塞斯说自己的改编是力求复原的,甚至拍电影时会把好几本《造梦的雨果》带在身上,布莱恩·赛兹尼克的绘本借电影灵感而来,因此颇多电影镜头式的画面表达,为了设法复制布莱恩·赛兹尼克书中的叙事经验,斯科塞斯甚至说自己毫不犹豫地按照原小说本身的镜头感安排分镜。

( 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拍摄现场指导演员 )
“我的小女儿将满12岁,在与她一起成长的这12年里,我学会了用很多儿童的视角看待世界,我可以很高兴地表达,如今在儿童的想象力范围内解释和想象在这个世界里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对我而言不再困难。电影相对文学匮乏的是内心世界的直接展示,那就是你可能无法了解雨果的内心想法和感受,当然可以用那些艺术化的镜头语言,但这样的一部电影不一定合适,因此我细腻地呈现了这个男孩的动人脸庞和举动,并在某种程度上对故事做出了变更,删除了书中的一些元素,也加入了某些我心中的影像,尤其是以3D出现时,能够涵盖到书中母题的许多范畴。”
最显而易见的增减集中于这样一些段落:雨果将乔治·梅里叶藏在壁橱里的画稿打翻在地,原著的过渡性情节,在斯科塞斯的影片里,漫天飞舞的画稿,一张张幻化成为梅里叶老电影里的真实影像,配合优雅的3D立体效果,自银幕轻盈飘零,既是一位父亲给女儿讲故事时饱满着爱意的妙趣,也是一位电影人对前辈拓路者的诗意深情。雨果到图书馆里借阅电影史著述,一部部经典电影便从书页跃然于银幕之上——《火车进站》、《工厂大门》、《寻子遇仙记》、《月光宝盒》。
电影梦想开始时的温度,斯科塞斯恰是用了最先进的3D数字技术重温。《雨果》是马丁·斯科塞斯的第一部3D电影,与技术狂人卡梅隆用《阿凡达》一石三浪的3D热潮相去已有时日,甚至曾经并肩的同辈(他曾与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乔治·卢卡斯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并称20世纪80年代四大导演,好莱坞“四杰”)也早已走在他的前面。多年前乔治·卢卡斯便预言3D即将成为王道,甚至彩色电影也会成为历史,他的6部3D版《星球大战》已在全球影院陆续上映中;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高调拍成了《丁丁历险记》,与好莱坞著名的技术狂人彼得·杰克逊密切合作,用最完美主义的精神挑战了3D技术的极限。斯科塞斯的审慎却常常被人们当做谈论故事与技术不相融的例证,“故事大王,便不必要3D”。
“1953年,我第一次看了安德鲁·迪托斯执导的《蜡像之屋》,那可能是当时制作上最出色的3D电影,那时我可还是个孩子。来年(1954年)上映的另一部电影《电话情杀案》,真叫我赞叹不已,希区柯克对3D的运用,与其说那是一种效果,更应该说是在辅助故事,那是聪明地用了3D来推动故事,也就是运用空间作为叙事元素。而且,我发现3D制作能提升演员的价值,仿佛看着一具立体雕像在移动,一切不再是平面,加上适当的表演和动作,变成融合戏剧和电影的呈现,但是又不同于两者。”
所以,斯科塞斯说自己对于3D媒介始终是很感兴趣的,也一直梦想能拍一部3D电影,在他看来,3D是从7岁到100岁都合适看的电影形式,也是所谓家庭电影的最佳形式。“有次我告诉女儿和她的朋友们,爸爸正要拍摄《雨果的梦想》,孩子们都知道这本书,他们异口同声道:‘这片子将是3D的电影,对吧?’我回答:‘是的。’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制片人,编剧还有视觉特效的同事们说,咱们得研究一下怎么拍3D了。”斯科塞斯如是告诉本刊。
马丁·斯科塞斯说,自己有关3D的野心,是真正的3D,而不是詹姆斯·卡梅隆/文斯佩斯公司的复制。“对导演而言,随新技术而来的是新的职责和新的思考,比如如何更好地运用这样的数字化记录和创作影像,采取怎样的态度处理电影美学上的过去,面对电影美学意义的未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雨果》是马丁·斯科塞斯第一次的大银幕3D故事,他用电脑虚拟再现了20世纪初巴黎的城市夜景,曼妙而又恢弘,也动人至深地在银幕上重现了百年前的经典电影片段,当然还有一代电影大师的人生曲折,以及一个孩子追梦的执著,贯穿其中也有对古老欧洲文明的赞美,对于战争和人性的反思。如斯科塞斯说,电影永远从脚下出发再与梦想紧密相连,我们都是追梦的孩子,都在为梦的延续竭尽全力,越走越远很好,但也该记住原点,这才真正在画一个圆。
马丁·斯科塞斯告诉本刊,作为导演,唯有用这样的方式,才可以抒发对那些曾经为我们捕捉旧日时光的电影家们的感激之情。“实际上我发觉随我成长的电影美学渐渐消失殆尽,我们往往不过是在因为某些文化诉求去保存它们,留给年轻人看看。事实上,你可能做不到完全同意约翰·福特在《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里的每一件事,或者对于《搜索者》的影像构成也颇有见地,但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个感觉我们的国家过去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这个世界曾经如何,一部电影可以放映做电影的时代人们的方方面面,比如如果真的存在某种陈规,那么真的就是有的,你不能抵赖说没有,因为谁都不能钻进电影里抹去那些痕迹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然而生活里可以,所以我更信赖电影一些。人有必要知道我们曾经身处何处以及我们将要面对何方,这是我们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
过去与现实的对话
这并不是马丁·斯科塞斯第一次在作品中进行“过去与现实的对话”。早在1967年,当他还是位踌躇满志的电影青年,带着第一部电影《谁在敲我的门》参加了芝加哥电影节时,这样的对话已经成为使他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谁在敲我的门》是一部低成本制作的半自传影片,讲述美国意大利裔青年J.R.的恋爱故事——他深深迷恋上金发女郎,甚至到宁愿召妓也无法与恋人同床的地步,因此在面对她因遭强暴不再是处女的现实时,内心产生深刻的厌恨。这是斯科塞斯最早期纽约意大利裔青年三部曲中的一部,影像、音乐、剪辑无不充满60年代精神,而那部电影的开头便是年轻人靠着给女孩历数西部片的角色,大段诉说自己对于约翰·韦恩的迷恋赢得芳心。电影里的J.R.明显在说着斯科塞斯说给女孩的话:“该大方承认喜欢西部片,要是人人都喜欢西部片,很多问题早就解决。”
马丁·斯科塞斯从来不否认自己对于电影史的迷恋,甚至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回忆自己最初踏上导演道路时的状况。“60年代的电影分为两派,一派推崇安东尼奥尼的《情事》,另一派信奉费里尼的《甜蜜生活》,我本人是支持《情事》的,因为那部电影步调很稳,那时我觉得任何慢的事务必然是严肃的,第一部短片(《像你这样的淑女在这种地方做什么》)我尝试也这么做。但实际上在拍这部短片的前两周,我看了《八又二分之一》,并且因其运用镜头之流畅与黑白影像之美完全被震撼,我更深爱上这部电影,第二部短片又开始对《八又二分之一》的模仿,这就是我的开始,坦白说,除此之外好像别无选择。”
从《谁在敲我的门》开始,马丁·斯科塞斯便是以高度个人化电影叙事和极端反叛精神征服好莱坞的。《愤怒的公牛》(1981)是斯科塞斯事业受困而蛰伏了三年之后破釜沉舟之作(1976年的《纽约纽约》因为试图突破好莱坞经典歌舞片而严重背离了观众趣味最终惨遭滑铁卢),也是影史公认为斯科塞斯个人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作品。影片开头马丁·斯科塞斯用每秒120格的慢速拍摄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拳击手在迷雾中独自练习,有意略过拳击手的面部,却给观众留下充分空间去体味银幕上身体、运动的优雅,配合意大利作曲家皮耶妥·马斯卡尼(Pietro Mascagni)的音乐,仅此一镜便带着观众走进了男主人公不屈精神和徒劳未来的两难之中,而这一镜至今常常作为好莱坞最经典镜头被提起,编纂进全世界的电影教材。
而斯科塞斯自己,每逢提起《愤怒的公牛》,最乐于谈及的却是如何从希区柯克那著名“沐浴段落”汲取了灵感,从而解决了自己的“拳击段落”的剪辑难题。“要知道那倒是我想起来那部电影就颇为满意的地方。过去不是过去,而是充满灵感的现在。电影史永远不会过期,这正是过去和现在之间不断进行着的精神对话。”
据说,在马丁·斯科塞斯的办公室里,电视机24小时锁定在放映各种经典电影的电影频道,从上世纪80年代呼吁业内重视柯达胶片的褪色问题,到90年代成立了电影基金会,协助各国电影档案馆发现保护修复影片超过500部,马丁·斯科塞斯身体力行着“电影史狂热分子的义务”。
当然他从没有忘记自己手中摄影机的书写功能,1995年的《斯科塞斯的美国电影之旅》,便是一部用4小时纪录片时间回顾20世纪美国电影史的影像著述,影片分为“导演的两难境地”、“导演是讲故事者”、“导演是魔术师”、“导演像走私犯”、“导演应打破旧习”五个部分,是客观史实与审慎而又热情的电影人视角最难能可贵的结合。
而同样4小时长度的《我的意大利之旅》则是本更个人化的电影教科书,马丁·斯科塞斯从自己的从影传记和创作评论出发,面对了更广义的意大利电影经验——从斯科塞斯家族的美国移民史到意大利战后电影史,从新现实主义罗塞里尼的《德国零年》到安东尼奥尼的《八又二分之一》。
“我爱电影,它是我生命的全部,希望有一天我是死在摄影机前。”如今,这位在纽约法拉盛的“小意大利”区出生长大、自小体弱多病,也曾立志成为神父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早不再是当年的“电影小子”,但仍在用如此意大利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于电影的痴迷。
(实习生朱婵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上一篇: 居家中,家长应对“神兽”有多难?
- 下一篇: 这个专业不交学费,毕业后还直接入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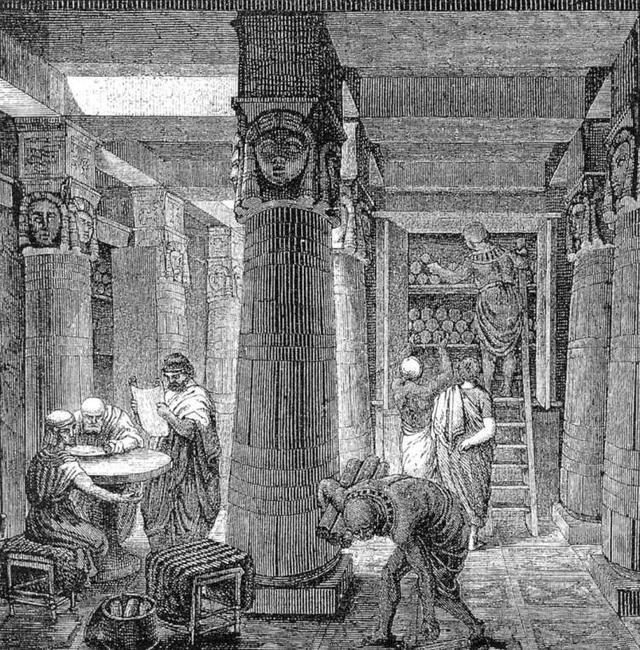

最新留言
说:写得非常好!
2020-10-28 11: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