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张天翼的人,都叫她“张师傅”——她自认为是个“文字手艺人”。最近这段时间,她几乎一直待在家中,为宅家准备的购物清单里,除了食物和日用品,还有一本“100款纸飞机的折法”。她想象着,在家里,每天站在朝阳或夕阳下,向着对面的槐树发送纸飞机的画面。

作家张天翼。/受访者供图
回忆起10年前,4月的巴黎,正值春末,天色渐渐灰暗,拉雪兹公墓里下着小雨,张天翼穿着薄薄的单衣,被冻得浑身发抖。墓园当时的样子,在她眼中就是一幅被雨线模糊掉的莫奈的画——沉睡的墓碑前,穿着雨衣或撑着雨伞的人们,肃立默哀。
画面感,对张天翼来说很重要。她刚开始写作时,会为了一个脑海中的画面而去写小说。画面的底色无论灰暗还是明亮,折射到张天翼的作品中,都是一体两面的,有悲观亦有乐观。现实中的缺憾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弥补,也会在写作中变得怪异和荒诞,在她看来,人可能都在不断“找补”。
画面感,对张天翼来说很重要。/图·pexels
生活中,张天翼会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投向爱情。她有一个能理解她所有情绪的丈夫小薛,让她在婚姻里安心做自己。然而,与父亲的长期积怨,使得当年那个没有得到正常童年的孩子,始终盘桓在她的体内不肯离去。
于是,她在《性盲症患者的爱情》里建立起一座城堡,好像是她给自己造的精神游乐园,城堡顶上插着一面旗子,彩色的布面上写着大大的“张”字——这是“张师傅”的城堡。而城堡里面,驻足着那个“怯懦”的孩子。
《性盲症患者的爱情》,张天翼著。
让不可捉摸的“天才”见鬼去吧!
张天翼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家里算不上富裕,但儿时的张天翼也没少喝果珍和高乐高。但她有个脾气暴躁的父亲,街坊四邻都知道“老张打孩子”。
有一次,六七岁的她被父亲骂了,贴墙罚站,低头落泪,眼泪一滴滴掉在地上,变成边缘不清的黑色圆点,错落排列。那一刻,张天翼的身体中似乎抽离出另一个自己,她用语句去描写那些泪滴,委屈和痛苦竟神奇般地消失了。那时她懵懵懂懂地意识到,“作家”就是描写内心感受和描写生活的人。
“作家”就是描写内心感受和描写生活的人。/图·pexels
从小学开始,不管是造句还是写作文,张天翼都比别人“写得好些”。这点小小的天赋,被她的父亲捕捉到了。从那以后,所有孩童的娱乐和游戏在父亲眼中都是浪费时间。听话的她,再没跟任何一个邻居伙伴玩耍过。
张天翼回忆:“在屋里读书,经常听到小孩在窗外念着口诀跳皮筋,感觉天堂跟我就隔着一堵墙、一扇窗,那种深重的孤独与沮丧难以磨灭地刻在心头,仿佛世上人分为两群,一群是正常的他们,另一群就是自己。”
直到十几岁,张天翼都被父亲管束着每天写日记,还会不定时被抽查。父亲一旦发现她漏写了,便非骂即打。张天翼还经常被父亲要求做一些超纲的语文题,每晚到了父亲给她对答案的时间,她都瑟缩等待着,像等待被处决的囚徒一般。
直到十几岁,张天翼都被父亲管束着每天写日记,还会不定时被抽查。/图·pexels
长大后,她开始用尽力气矫正、治疗由父亲造成的伤害。“十几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在跟父亲做斗争,但有些东西失去就是失去了。裹过的‘小脚’再放开也是‘半大脚’,还是得垫着‘棉花’,带着只有自己感觉得到的‘残疾’,在人群中佯装正常行走。”
在张天翼看来,由于时代的缘故,上一代父母郁郁不得志的居多,再加上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很多父母把自己的成功欲嫁接到子女身上。
“天才是礼物,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对于成长期的孩童来说,更多的是痛苦。”张天翼提起看过的一部瑞士电影《想飞的钢琴少年》:6岁小神童维特显露出钢琴天才后,被所有人寄予厚望,然而,为天分所苦的维特,宁愿从楼上跳下、佯装受伤失去天分,也不愿再做神童,最终他如愿以偿地进入普通学校,交到了普通的朋友。
电影《想飞的钢琴少年》剧照。
“幸好我不是天才少女,也幸好世上有学校的存在,而我父亲也还不敢托大(编者注:北方方言,有自大之意)到不让我上学。”
如今,张天翼已经不再是孩子,更是明白了“天分”应该是上天馈赠给孩子的礼物,并不是给父母的,父母不应该把它当成自己的资产去对赌。也有人质疑,如果不是父亲的严厉管教,她有可能不会走上今天的写作道路。张天翼说:“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不辜负天分,但我认为最首要的,是让孩子获得正常人能获得的一切,比如同龄的朋友,以及一切在这个年龄应该享受到的快乐。”
张天翼认为父母不应当将自己的压力施加在孩子身上,应该让孩子享受童年的快乐。/图·pexels
在张天翼看来,人类的文明进程,也许在某个时间点上被某个天才的某项发现推了一把,但前进是历史的必然,人类最终都会吃上熟食、用上电灯、开上汽车、接入互联网。
后来,张天翼在《天才少女》的影评中写到,比起一个孩子的鲜活生命和无法重来的人生,让缥缈得不可捉摸的“天才”和“改变历史”见鬼去吧!
爱的“白魔法”与“黑魔法”
比起不堪重负的童年,张天翼把后来遇到的爱情看作上天对她的弥补。每次和别人聊完自己的情感状态,她都是一副“抱歉,又撒狗粮了”的表情,那是一种难以掩饰的幸福。在她眼里,小薛几乎是一个完美丈夫。
小薛曾对张天翼说,遇到她之前,他看到的人都是不分性别的,遇到她之后他才萌生了对异性的认知,感官好像醒了过来。
张天翼与丈夫小薛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性盲症”就是这样。小薛给了张天翼写作的灵感,后来,她写了《性盲症患者的爱情》。她在书中写到,自幼因患有“性盲症”而不辨男女的青年,看到了可能一辈子就只能辨别出这一次的那一位异性,当他们遇到正确的人,在黑白的世界里,好像只有那一个人是彩色的。
而张天翼对爱情的最初认知或者与人鱼不无关系。儿时,她拥有80后最普遍的童年经历——看《安徒生童话》,她爱上了他笔下的小美人鱼,后来大一些受到世界名著的影响,她又喜欢上了王尔德书写的人鱼。而这些有关人鱼的故事“都留下关于爱情的伟大篇章,一代代孩子为小人鱼哭出的泪,足能灌满一个大西洋,其中就有我贡献的一池子”。
《王尔德童话》,王尔德著。
颇具童话色彩的爱情,如同被施加了“魔法”。在张天翼的小说中,经常能看到充满暗黑美学的爱情——一半是童话,黑暗却闪烁希望;一半是现实,冰冷却又点缀奇迹。
当然,张天翼也写圆满的爱情、健康明媚的关系。用她的话说,爱情的“魔法”,既有“黑魔法”,也有“白魔法”,我们想从爱情里面不断地获得力量,势必会产生贪念,会有无法控制的欲望,有的时候甚至会越界,就像“魔法”也会有失控的时候。在很多童话故事里,那些修炼“黑魔法”的人,即使获得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也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并且遭到反噬。
“我喜欢去想象,在爱情的关系里,代价到底是什么,以及力量反噬的结果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圆满的爱情更难书写。”张天翼说,“就像韩愈说的——和平之音淡薄,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
张天翼明白,在她的精神角落里,需要去化解的,有小时候被父亲的“黑魔法”所冻结的爱。/图·pexels
愉悦的爱情,让人觉得浅薄,反而是经历波折或者有一些缺憾的东西,才容易被人铭记——当然,这是一种“讨好式”的写作。
张天翼明白,在她的精神角落里,需要去化解的,有小时候被父亲的“黑魔法”所冻结的爱。只是这样的一天,还没有到来。
也因此,面对读者,张天翼总是一副“讨好”的样子,骨子里的“怯懦”让她急切地想要“抖包袱”,像一个刚学会说相声的人。参加过张天翼签售会的读者曾经提到过,“张天翼很可爱”,每次给读者签完一本书,都会对着字迹吹一会儿,怕油墨粘连了扉页。在创作上,因为害怕读者觉得上一段不好看,在下一段就会将小说遗弃,所以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写出让读者开心的东西。
张天翼似乎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并不利于写作:“一个理想的写作者的性格,应该是坚定和理性的,对于读者的批评和赞美,都能做到像个独裁者一样,并且自始至终贯彻自己的想法,在文学的境地上矗立自己的建筑,这是我一直想要去克服的。”
给现实生活找到出口
这两年,张天翼开始把自己的写作视角放在一个个普通人身上。即使是最熟悉她的读者,也会惊讶于这个躲在安吉拉·卡特式童话世界里的“小女孩”,一夜之间“长大了”。
然而,这些变化并不突兀,或许这是沉积于心许久的生活在某个合适的时刻重新生发出来,让她与现实达成了共鸣。
张天翼生活照。 /受访者供图
求学时,张天翼坐着火车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她看到并感受到火车这个特殊的密闭空间里,陌生人被迫亲密无间紧挨在一起。这种她体察过的“至亲至疏”的关系,被她写进了《我只想坐下》。
“那些微不适,来自早晨抢厕所期间,坐上还带着别人体温的马桶坐垫;来自洗澡时看到地上两滴血的恶心;来自做饭时忽然发现有人用过菜刀和砧板而且没洗干净……”张天翼之所以能够写下这段让北漂租房者“心有戚戚焉”的文字,跟她有着20多年的租房经历有关。
自幼她便跟着父母租房住,直到高中,父母才买下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张天翼曾经考究过从古至今的租房历史,并脑洞大开,想到这样一个情景——寒武纪,生活在海底的一种四角虫,它的生命只有一天,但这仅有的一天也要为“买”上一处珊瑚房而耗尽终生。
当然,除了这些现实题材之外,张天翼被注意到更多还是源自她对女性的观照。
《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著。
张天翼小时候读过《乞力马扎罗的雪》,许久之后,那雪白的巨大山影,似乎依旧印在她心里。这座雪山后来衍生出了张天翼一本名为《如雪如山》的小说集。
《如雪如山》是一本女性视角的小说集,她笔下的这些名叫“lili”(立立、莉莉、丽丽、栗栗)的女孩,她们的悲喜与爱恨,与这世上最普通女性的情感既迥异又相通。
在张天翼的成长经历里,她与母亲的感情算是最要好的。几年前,她陪母亲去做了一场取出节育环的手术。由于上环时间太长,环已经和肉长在了一起,连医生都责难母亲怎么现在才来。
《如雪如山》,张天翼著。
听到医生的话,张天翼心疼不已,她问母亲会不会痛。母亲说当然会痛,但是女人生来就是要吃苦的,老天爷让女人每个月都流血、肚子疼,就是要锻炼女人的忍耐力。
从那以后,张天翼开始思考女性的生理疼痛。母亲是她最了解的女性,这位上一代中国家庭式普通妇女,一直都以吃苦为荣。是环境塑造了她们那代人的观念吗?如今时代进步了,女性身体上的那些细微感受却仍旧被人们忽略,甚至女性自己也选择了缄默。在张天翼看来,这些感受需要说出来,也需要有人替她们发声。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还能够通过女性视角写东西,写作至少是一个出口。”/图·pexels
张天翼回忆自己20岁以前,曾一直被父母教育要忍辱负重,做一个“贤妻良母”,直到她懂事之后,才慢慢地把思想上的皮褪掉,她说:“作为生活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人,我们都避免不了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就像恐龙在白垩纪开始进化出羽毛,学会了滑翔,最后才进化成为鸟。”
在张天翼看来,多创造一个自己认可的好的世界、好的环境,在小说里面把它说出来,一定是有用的。生物的种群会反过来影响生态环境,而女性与社会环境之间,肯定也是有相互作用关系的。“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还能够通过女性视角写东西,写作至少是一个出口。”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上一篇: 俞敏洪要做电商学院 / B站付费视频,你会掏钱吗?
- 下一篇: 《梦华录》的最佳配角,我提名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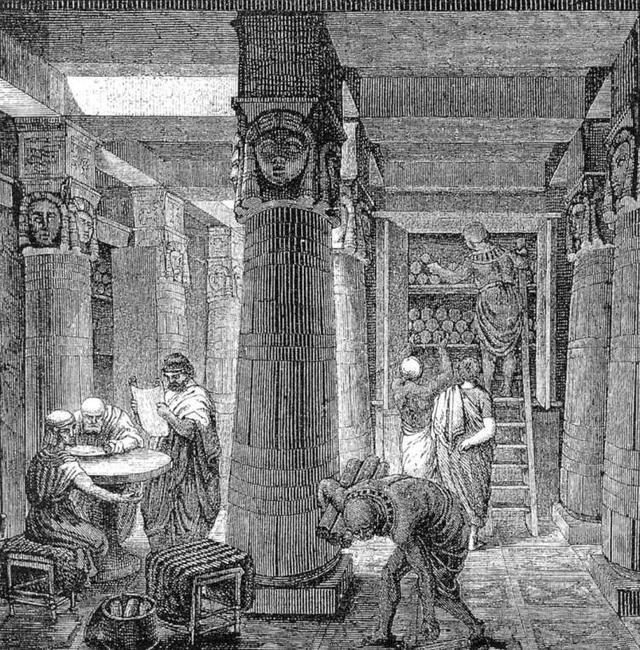

最新留言
说:写得非常好!
2020-10-28 11: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