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百年时间,中国考古学目前面临着一个空前复杂的状况,即如何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向错综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运作研究。仰韶文化当然也在这个状况之中,在有一定物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考古学者们面临着对整个仰韶社会复原的难题。 虽然仰韶文化是最早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文化,但对仰韶的研究是有迟滞的,论社会研究层面,赶不上良渚,也赶不上石峁;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学界对仰韶晚期以来到龙山时代,再到进入“三代”(夏、商、周)更为关注。有关仰韶,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什么是“仰韶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围绕仰韶文化的考古学命名和界定,一直以来在学界颇有争议。比如苏秉琦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仰韶发掘65周年时)提出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不超过西起宝鸡,东至陕县(今三门峡)一带”,后来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仰韶文化解构开来看,而近年“大仰韶”的提法又颇为流行。首先想请您谈一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仰韶文化?从时间和空间上该如何界定仰韶文化?
赵辉:先说仰韶时代。在学术史上,严文明先生首先提出了“龙山时代”的概念,也就是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那个时代,黑陶的广泛使用成为最重要的时代特征,除了一系列物质标志之外,社会发展程度、经济文化面貌也都比较明确。但当时“仰韶”并没有那么清晰,既然有了“龙山时代”,那么龙山时代之前的那个阶段怎么叫?学界逐渐默认称其为“仰韶时代”,也就是龙山时代之前的2000多年,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这个阶段。
仰韶文化处在仰韶时代,这一点无可厚非。但仰韶时代不仅仅包含仰韶文化这一种面貌,与它同时存在或时间上交集很久的还有其他考古学文化,比如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北方的赵宝沟-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北辛-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是其中的一块,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块。
再从地域上来看,仰韶文化的分布大致与我国黄土地区的分布范围差不多,也就是黄土高原,从陇东一直到陕北,向东包括整个山西,郑州以西的大部分河南地区,直到豫南的南阳也算在内。郑州有点像个分水岭,郑州以东的河南地区算不算仰韶文化,这个不好说。因为郑州以东是“黄泛区”,历史上黄河泛滥带来的灾难,对古代遗址的损害极其巨大,现在也很难找到遗迹,所以豫东这一块不好判断。而豫东再往东到达山东,就是大汶口文化的范畴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大框架下,对仰韶文化的分期是否也更清晰了?
赵辉:现在学界对仰韶文化的分期,主流的看法是分为三期或四期,争议不大。在每个大的分期里,每个地方又有不同。有些学者比较强调这个“不同”,于是就把大的仰韶文化拆分开来看。我个人不太主张这种做法,因为每个大型文化,内部都会有差异,因时因地总会存在地域性的、小规模的特征,当把它们放在大格局之下来看时,它们的文化面貌是趋同的。
在考古学上,“文化”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只是我们为了方便今天的叙述,根据客观形势、客观情况,做出了今天意义上的划分。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杂糅进去一些主观因素,所以不必在“文化”“类型”这些划分和名词上过分较真儿,这些都只是为了方便研究而附加的概念和称呼。我们做考古学研究、做历史研究,除了如何界定概念,真正重要的是去关注这些文化面貌所反映的那个社会,别丢了这个大目标。

从物质文化研究到复原历史社会
三联生活周刊:通过对仰韶文化的百年考古,现在学界对仰韶文化的认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赵辉:这个要从考古学是怎么做的开始说起。先得看物,考古学在通过物质文化遗存来研究历史的时候,大致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有什么、什么样;第二步是怎么分期、怎么分区,或者叫怎么划分地方类型。首先把大圈划出来,里面再划小圈,分几个大期,不同期里面这些小圈又是如何变化,和周邻有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关仰韶文化的分期、分区、地方类型这些基础问题,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等这些老先生都写过很多文章,他们个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思路是一样的。这些我们称之为物质文化史的研究。
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有两个作用:一是给中国古代文化搭建一个年表,或者说谱系。史前史是没有历史记载的历史,考古遗存也无法直接反映谱系,所以必须通过物质文化先搭建一个框架,一个历史研究的时空坐标。如果没有这个坐标,就不知道时间,不知道地区、地域,这是史前考古的最基本需求。第二是通过对错综复杂现象的梳理,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的大趋势。在仰韶时代,这个历史的大趋势是多元的、一体的,同时也否定了黄河是中华文明唯一起源的说法,长江流域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西辽河地区同样重要。在我们熟知的中原地区之外,还有一个大圈,这些地区长期复杂的人类活动,最终“运作”出今天的中国,变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实体。那么在时空坐标的搭建之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进而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历史观。这个史观,如果不琢磨考古材料,单从文献上琢磨是没有的。史前考古学的不断更新,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传统的史学观,或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观,这是我们所说的物质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
研究物质文化史是第一个大阶段,第二个大阶段是讨论错综的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运作,也就是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其实考古学一直以来都有这个诉求,不过从逻辑上来说,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在前,对古代社会的复原研究在后。首先得认识东西,然后再琢磨东西背后的事。
中国考古学自建立以来,受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比较大:一是我们接受的是西方现代考古学的系统,从观念上、思想上都不是从零开始,受影响最大的这个流派就是从物质文化到背后问题的研究思路;二是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在物质文化史研究还不充分的阶段,受到了苏联考古方法的影响,当时苏联学界注重古代社会的探讨,这个思想很超前,某种程度上也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为它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经济发展形态。在此影响下,我国的考古界也开始尝试去找出一个氏族社会,这时有了半坡遗址的发掘,其考古报告就叫作《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可以看出它不仅将出土遗物分期归类,而且直击社会本质的探讨,非常前卫。但是由于整体田野考古还有很多工作没做,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尚不充分,这种超前的考古研究很难形成连续性。
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一些重大遗址的发现,古代文明的大问题再次摆上台面,古代文明的形成、起源被不断提及,红山、良渚、大地湾这些大型新石器时代遗址成为焦点,大家就开始思考中国文明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那么仰韶文化的社会是如何发展的,早期、中期、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文化又是怎么一一衔接更迭的,这些问题在这个大思潮中变得重要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考古学才开始尝试系统性地摸索该如何研究古代社会的本质,到现在不过30多年的时间,还“幼稚”着呢,还没琢磨透。
研究古代社会,依赖田野考古。通过田野考古工作提供的一套物质文化材料才能进行社会研究,包括出土遗物、地质地层、聚落结构、自然环境、自然遗存、动植物组织、DNA提取等等,构成社会研究的方方面面,这时考古学所面临的问题就复杂多了,谁能把一整个社会全都弄明白?
现在,中国考古学就面临着一个空前复杂的状况,仰韶当然也在这个状况之中,也就是在有一定物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面临着对整个仰韶社会的复原。然而,虽然仰韶文化是最早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文化,但对仰韶的研究是有迟滞的,论社会研究层面,赶不上良渚,也赶不上石峁;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学界对仰韶晚期以来到龙山时代,再到进入“三代”(夏、商、周)更为关注。有关仰韶,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新石器时代的信仰与原始宗教
三联生活周刊:您一直在强调物质文化史研究对考古学的重要性,从出土文物来看,同为新石器时代的几个重要文化,比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其遗物都以玉器为代表,其精美程度、工艺的复杂度、内涵的精神性都超过仰韶文化的彩陶。李伯谦先生也因此提出中国古代进程中的两种模式,即“神权”和“王权”,红山、良渚是神权社会,仰韶是从军权到王权的社会。我们该如何理解“神权”和“王权”这两种模式?
赵辉:我认为没那么简单,李伯谦先生的理论是一个高度的概括。首先,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红山和良渚。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信仰分别是什么,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只能通过目前流传下来的可能与其精神信仰最密切相关的那些图像资料、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来推断当时人们的信仰模式。可以看出,红山与良渚的信仰模式是全然不同的。红山没有一个信仰的主体,玉器雕刻里什么动物都有,龟、鸮、天鹅、蜥蜴、蝉、蛙,各种各样的,也有一些人像,也是各种各样的,没有统一的,都是不同的样子。而良渚不然,良渚玉器上的雕刻几乎都是一个人骑着猛兽,这不是自然里的东西,是人创造出来的形象,而且是一个极其统一的造型,每件玉琮上的雕刻相似度都很高。也就是说,良渚有一个集中的信仰,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神教”,而红山是多崇拜的,更像是一种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是从自然里生发出来的。
在这两个处于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社会里,宗教信仰都在整合社会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虽然我们现在仍不清楚具体的宗教内容,但应该是差别很大的。如果将它们都“打包”归为神权社会,未必妥当,因为其内核全然不同。
再来看仰韶。我们从现在仰韶的出土物来看,基本上可以判断仰韶的信仰也是一种自然崇拜,它没有统一的形象,鱼、鸟、花卉是出现比较多的,但其实也有蜥蜴、壁虎这种东西,它更像是家里周围附近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田野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这些图像里,几乎看不到哲学,看不到概念。而在良渚的玉器里,是可以明显看到概念与哲学的,比如英雄人物的形象、人定胜天的理念,它反映出人和自然,甚至是人和宇宙博弈的关系,而在仰韶文化里是很难看到这种高层次的、形而上的东西的。
三联生活周刊:可不可以理解为,在仰韶文化里,宗教的影响是比较弱的?但在仰韶所处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仍然是普遍存在的,仰韶也不例外?
我自己在看中原地区仰韶彩陶,尤其是仰韶中期的庙底沟彩陶时,几乎感受不到这些纹饰是有神性的,而在晚期的马家窑彩陶纹饰里,精神性强烈得多。我会把前者看作图案,而后者则是图像。
赵辉:咱俩的感觉差不多。当然,仰韶文化里很多繁复的彩陶花纹我们至今也不太能理解。这些彩陶花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也是一种共同意识?是一种能达到宗教层面高度的共同意识,还是仅仅是一种潮流、爱好和时代审美?这个说不准。有学者认为它存在着精神性的一套系统,但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把仰韶与红山、良渚相比,其宗教信仰的高度应该没那么高,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有点保守了。
良渚出土了那么大的玉璧、玉琮,这些东西并没有实际作用,从功能上根本无法解释,它明显地体现出形而上的宗教性。但仰韶没有这些,仰韶的彩陶甚至是玉器,都还是很平实、很日常、很普通的器物,一种田园生活的风格。
其实在每种文化、每个社会里面,都有一套精神性的东西,但状态不同,模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在良渚文化里,宗教和信仰可以把这个社会整合成一个等级十分分明且运作高效的形态。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仰韶背后的那个社会,宗教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

如何理解“古国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经在《“古国时代”》这篇文章中谈道:“公元前4000年或稍晚至公元前2300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质农业村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总人口的增殖,导致了整合聚落群的政治行为,造就了‘古国’的聚落形态。”自从发现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河洛古国”的概念也被学界提出,一度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在仰韶文化里,我们具体该怎么理解“古国”这一形态?
赵辉:“古国”是借用了文献上的一个说法,当然,学界也有很多反对的看法。一种反对声音认为,在全球考古史上,对国外文明起源的研究里有一套理论,即“游群-酋邦-国家”,这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提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种与之相似,即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托马斯·摩尔根(Thomas Morgan)强调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这个系统。但是摩尔根主要研究的是早期人类的婚姻制度,他的这套系统重点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产生、权力的分配等问题。
当西方考古学中已经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发展的模式框架之后,我们在研究中国的社会形态时,自然会反思,中国的历史有没有自己的特点?会不会在这个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里被忽视掉了?我们搞历史研究的,除了研究历史的普遍过程以外,还必须特别关注历史的特殊性。而我们的长远目标就在这里,要看中国历史有没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什么样的。因此,在谈到史前社会形态的时候,就借用了“古国”这一古代文献里的说法。
先秦文献中,时人回忆上古天下形势时会用“万国”“万邦”的字眼,比如《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吕氏春秋·用民》中的“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等等。当然这里的“万”是虚数,“很多国”的意思。那么,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前的社会结构,以及这个社会是怎样从一种简单的、平等的、平均的社会结构,变成一种复杂结构的过程时,“国”,也就是文献中的“万国”很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可否把“古国”理解成一个迈向文明的标志?
赵辉:我的那篇文章《“古国时代”》,其实并没有对任何一个古国进行深入讨论,只是提倡一种方法。比如在仰韶文化的早期,各地的发展是比较平均的,半坡、姜寨等聚落都是三五万平方米,围成一个圈,里面有大房子、小房子,但是很难看到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在生产生活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形成一种平均、平等的状态,这远远谈不上美好,就是一种不得已的平均状态。这种情况在仰韶时代早中期的大多数地区也差不多,有的发展快一点,但是凤毛麟角。而从仰韶文化中期,也就是庙底沟时期开始,社会变得复杂起来。复杂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一群聚落里出了个头儿,我们叫它中心聚落。中心聚落就是这个社会群体里最有势力的一支,开始可能是松散的,通过不断地整合,逐渐成为一个政治实体。
在此之前,聚落的分布是一种自然状态,比如要开展农业生产,就要找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就产生了人口的聚集。但当政治实体出现后,这个大聚落可能占地面积较大,高等级的建筑、使用器,大型的墓葬就陆续出现。因此,古代文献中出现的“国”并非达到国家的程度,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氏族组织、部落组织等。我们从这些中心聚落不断复杂化的过程,可能触碰到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过程,所以“古国”指的是这层意思。
这些古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特别有实力的古国就开始整合,从中心聚落的内部整合开始,进而扩散到周边聚落,彼此之间由冲突而产生新的整合,当某个中心聚落把周围的古国整合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更大的权力中心就诞生了。有学者将这个更大的聚合称为“邦国”或“方国”,总之要跟中央帝国区分开来,比如良渚和石峁这种等级的,它是区域性的中心,可以看作方国。但无论是邦国还是方国,都是商代的名词,史前史中的类似形态该如何称呼,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回到“古国时代”。在“天下万国”的时代,古国是此起彼伏的,它们都是从一个平均的状态发展到复杂的,但有的地方先产生,有的地方又没落了,生命周期各不相同;有的又是一个分裂成两个、三个,有的是几个整合到一起,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而且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不同环境背景下产生“古国”的原因会有不同,我不知道仰韶文化中这些“古国”具体是如何产生的,可能与农业生产相关,可能与矛盾和打仗相关,可能与对剩余产品的控制相关。
我们说仰韶之后的龙山时代,陶器的生产水平已经极其发达,甚至出现了批量生产,这种批量生产显然不再是为了满足个体的家庭需求,而是要供给很多家庭甚至族群,这样就有了交换和市场,成为一种商业生产。因此山东考古所的孙波认为,龙山时代社会复杂化的主要原因是,从市场行为里产生的公共管理这套制度,被运用到社会组织中。我想说的是,这种“古国”形态,或者说更高级的“方国”形态,是一种此起彼伏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仰韶时代呢?
赵辉:在仰韶时代,庙底沟时期(仰韶中期)是一个很大的繁荣阶段,但在这个时期,我认为目前还没有看到能够称之为文明的种种迹象,这与田野工作有关。比较重要的遗址有河南的西坡、北阳平,陕西的泉护、西关堡,但西关堡这个遗址现在已经彻底没了,严文明先生告诉我这个遗址有上百万平方米,他不太确定其主体是仰韶中期的还是晚期的,可惜现在已经没了。
而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各地的独立性发展起来,山东、甘青地区都有丰富的面貌出现。原本在庙底沟时期不太发达的郑州地区,在仰韶晚期反超了豫西地区,出现了双槐树、大河村这样的大遗址。再看陕北地区,从仰韶文化早期到中期,重要的遗址都不算多,但是到了庙底沟二期(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的过渡期),社会开始变得发达,石峁的社会复杂度远远超过了仰韶中期那些聚落,成为北方的一个超大型社会聚落。石峁与几乎同时代的位于晋南的陶寺遗址,等量齐观,是当时并驾齐驱的两座大城,其社会发达程度是仰韶时代聚落难以企及的。从这种聚落中心的不断转移,也能看出社会复杂化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过程。

“100年的时间,能琢磨出这么多事儿已经不错了”
三联生活周刊:学界有一种风尚,是将炎黄五帝等上古传说与仰韶文化的考古一一对应,试图从田野考古中找到佐证。对此您怎么看?
赵辉:这是中国考古学传统中的一种嗜好,因为我们有传说,大家都想往上靠。这不只是考古学,对于做上古神话研究的学者,也会对此惯性地刨根问底。但是因为目前这个阶段没有文字,这些不可证明之事暂且聊备一格,除非未来在相关遗址中出来文字佐证。我们更应该感兴趣、深入研究的是它的社会,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如何发展而来的。进行你说的这方面的研究也并非是错误的,但是整个学科不能往这个方向发展,不能这么做。
考古这个事儿,凭借田野材料可以把一个问题说得非常具体。比如一个房屋基址上,这座房子塌了之后恰好很多东西没来得及抢救出来,那么有可能推断出,这个房子多大,大概是个几口之家,哪里是睡觉的,哪里是做饭的,哪里又是做食物加工的地方,这些场景可以还原得非常具体,是可信的。但若一定要和文献上的具体人物对应起来,一定要有极其可靠的材料,而非推断,否则不足为信。
我们做考古的,就是从田野材料中看到一个个具体现象,把它们一一排列出来,这样就能看到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面貌。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提到仰韶文化,通常会认为现在的河南境内是中心,一是因为最早的发现地仰韶村在河南三门峡,二是因为庙底沟、双槐树等重要遗址也在河南,由此也引发对“最早的中国”、“最早中国之前的中国”(以二里头为“最早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化圈”等不同概念的讨论。可否把“最早的中国”、仰韶文化、中原地区关联起来,得出一个类似于“在中国中原地区产生的仰韶文化是最早中国的雏形”这样的初步结论?
赵辉:有学者认为庙底沟是“最早的中国”,也有人主张“最早的中国”可能还要更早一点,当各个文化之间开始产生交流,从底层的交流逐渐向一体发展,就构成了中国的雏形。我个人还是保守一点,因为我考虑到史前文化这种此起彼伏的变化过程。在我看来,在中原出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核心,是二里头,这种迹象从龙山时代就开始有苗头,到了二里头时期诞生了中原权力中心的实体,而后的商、周都落脚在中原(不是狭义的中原即河南省,而是广义上的黄河中游地区)。
在双槐树遗址(仰韶晚期)发现之后,人们会将它看作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心,它确实是一个超大型聚落中心,但它与二里头以后的中国文化面貌是脱节的,连不上。在龙山时代之前的庙底沟二期,也就是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把仰韶文化秩序打破后又重新整合的阶段,目前学界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还不算充分,但它是打破仰韶秩序和传统的。所以中原地区真正成为中国的中心,成为一个夯实的政治实体,要到二里头。
三联生活周刊:那庙底沟二期打破了仰韶传统,又变成了什么新的面貌?
赵辉:这不好说,缺乏田野资料。从文化上面我们能看到打破与重建的现象,但这个现象究竟是什么内核,还没法说。考古学要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一步一步按逻辑走到这里,最终的愿望是复原古代历史,但考古学在中国,终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能走到目前这儿,我们能知道目前这些已经不错了。100年的时间,能琢磨出这么多事儿已经不错了。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上一篇: 纸吸管,想说爱你不容易
- 下一篇: 《罐头小人》:乏味生活的拯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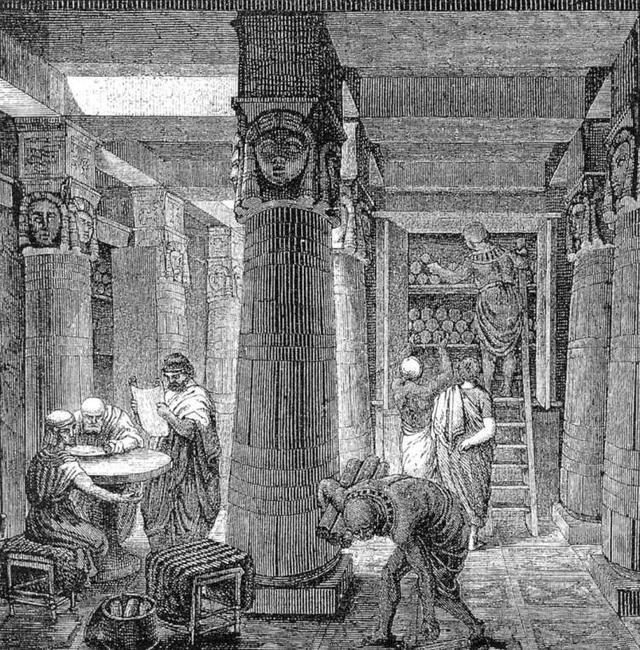

最新留言
说:写得非常好!
2020-10-28 11:15:56